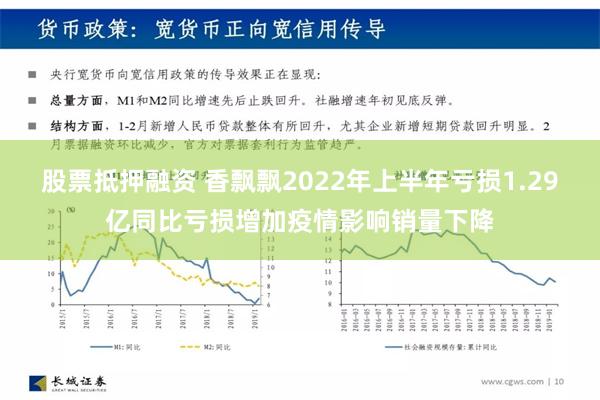【免责声明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与和讯网无关。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、观点判断保持中立,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、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。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。邮箱:news_center@staff.hexun.com
▲图/受访者提供
“人人都要应对‘不确定性’:年轻人要处理生活中种种不确定,老年人不得不面对死亡何时到来的恐惧。”
脆弱的爱情、危险的婚姻、迷茫的青年、孤独的老人……瑞士作家彼得·施塔姆(Peter Stamm)的文字冷静而克制,却在简洁、疏离的叙事中,将普通人的欲念和挣扎刻画得纤毫毕现,外界评论其作品有着“足以燃烧的冷峻”。
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
文 /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
编辑 / 周建平 rwzkjpz@163.com
作为瑞士文坛的中坚力量,施塔姆的创作可谓多产,其代表作包括《阿格尼丝》《如此一天》《七年》《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》等长篇小说,以及《在陌生的花园里》《我们飞》等短篇小说集,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9种语言。
施塔姆曾于2007、2010年两次访问中国,2024年10月上旬,这位荷尔德林文学奖得主再次访华,在沪期间接受了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专访。
“每次来上海我都感叹:这里交通发达,出行便利。在中国,尽管看不懂、听不懂你们的语言,但我总能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。这里的人很友好,也不复杂,我认识的那些德语教授非常有趣,他们经常开玩笑,让你感到放松。与此相比,欧洲气氛拘谨,我好像必须遵守1000条规则才能融入社交。”
施塔姆1963年生于瑞士魏因菲尔德,做过夜班门房、会计、医院护理师和记者等多种职业,他曾在大学修习英语文学、心理学、信息学等专业,游历过纽约、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等地,为《新苏黎世报》《每日导报》等报刊撰写文章。
1998年,施塔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阿格尼丝》在瑞士出版,翌年获得奥地利萨尔茨堡劳利泽文学奖,作品被选入德语国家中小学生读物。《阿格尼丝》奠定了施塔姆在德语文学界的地位,在这部早年代表作中,故事叙述者指出,他爱阿格尼丝,跟她在一起很幸福,但“只有当她不在的时候,我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。我的自由对我来说一直比我的幸福更重要”。
如何在生活的漩涡中追寻自由一直是施塔姆的创作所探讨的主题,《阿格尼丝》出版20年后,他又创作了与其呼应的《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》,凭借这部新作摘得2018年瑞士国家图书奖。施塔姆借书中叙述者透露:“现在我才明白,爱情与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,而是相互制约,一个没有另一个是不可能的。”
施塔姆的多部作品都聚焦于刻画当代瑞士人的爱情和家庭生活,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《七年》中,他构想了一名男子为欲望纠缠的、危机四伏的婚姻,借书中人物的心理独白,施塔姆给时代下了份诊断书:“他们的道德想象偏向狭隘,但他们理解人性的弱点,准备原谅一切。”
女人看似弱者,但其实她们都很强
南方人物周刊:早年写作《阿格尼丝》时,小说标题直接用了女主人公的名字,多年后与之呼应的中篇《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》则用了个相对抽象的标题,说说这个标题的来源,以及两本书之间的关系?
施塔姆:这个标题其实受到加缪《局外人》的启发:当主人公默尔索意识到他会死、会被处决,因为他杀了人,那一刻,他谈到了世界的甜蜜和冷漠,他接受了自己将被处决的事实,既有对这世界深情的眷恋,又带着平静的决绝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这个标题差不多引自《局外人》。
我认为《阿格尼丝》中,小说战胜了现实,因为书中女主人公在虚构的结尾死去,但不是在现实中。但在《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》中,女主人公最后表示:我不再玩你的游戏了,我要离开。这一次现实赢了,我觉得这是好事。写作《阿格尼丝》时我还是个冲动的年轻人,现在自己到了年纪,我支持现实获胜。
南方人物周刊:“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较量。玛格达莱娜赢得了几乎所有我们后来决出胜负的战斗”(《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》),男女关系是你一直在写的主题,你觉得亲密关系中经常伴随着这种“争胜负的战斗”?
施塔姆:我也不确定,但至少我喜欢自己书里那些强大、厉害的女人。这个世界上有好女人,也有坏女人。玛格达莱娜不是坏女人,她非常强,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在我看来,大多数女人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在中国也是这样吧?女人经常看上去是弱者,但她们并不是真的软弱,我觉得女人都很强大。
南方人物周刊:长篇小说《七年》中,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冲突体现在他们原生家庭的阶级差异。有种说法,婚姻要“门当户对”。
施塔姆:哦,是吗?我觉得在瑞士这不太重要,也许因为瑞士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社会,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什么阶级。当然我们有富人和穷人,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属于某个阶级,也许有些圈子不对所有人开放,但没人特别“重要”,也没人特别卑微,或许这也是小国的优势,人人都相对平等。
平等对于瑞士人而言非常重要,如果某个人极其成功,人们就不再喜欢他了,这无形中也成了我们的传统:每个人都保持低调。当然,这也未必是好事,一旦你成功了,就可能招来嫉妒。
我觉得唯一获得成功但不招人嫉妒的瑞士人大概就是罗杰·费德勒了,他很友好亲切,即便已是大红人,他从不骄傲,也不会宣称我很伟大,他总是很谦虚,所以人们喜欢他。他是个超级明星、网球天才,不过我觉得他有些无趣,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,回答得很简单,作为记者我可能没什么兴趣采访他。
南方人物周刊:说说你当记者的经历,当时都是做哪些方面的报道?
施塔姆:我们通常选定一个主题,去一个地方待上一周,写作关于当地的深度报道,通常是那类专题长文。很遗憾,现在媒体已经不发表这类深度报道了。例如我以前报道过北爱尔兰的冲突、挪威的少数民族萨米人、巴黎医院里经受战争创伤的老兵、伦敦剧院的校园项目……让我想想,我还做过关于墓地的报道,那个墓地葬着一些无名氏:他们的尸体被海水冲上了一座小岛。
南方人物周刊:早年你曾修读心理学,这段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?我发现你在作品中很少去分析笔下角色的心理,基本是让他们以行动来展示自己。
施塔姆:我学过心理学,但我没有完成学业。(笑)比起心理学,我觉得文学更能让我见识人性,某种程度上比心理学显示出更多真实的人性,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作家。我一直热爱文学,当初选择心理学是因为我觉得文学要写人、我必须研究人,后来我才意识到学习心理学不能真正帮助我理解每个人,也许它能帮助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,但它不能真正教会你读懂人性。人性要复杂得多,我认为文学是描述和研究人的理想手段。
学习心理学时,我曾有机会在心理诊所工作,我挺喜欢在那里工作,你会看到很多异于常人的案例,有几次真是超出我对人类经验的理解,有些是心理问题严重的病人,我说他们“有趣”也许很刻薄,但他们确实很有意思。
现在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觉得孤独
南方人物周刊:你多次提到喜欢海明威,不过阅读你的小说感觉与他的作品风格迥异,不知海明威的创作对你有哪些影响?
施塔姆:在我看来,海明威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世界,而不仅仅是创造句子。当我阅读他这些书时,我感觉自己身处另一个不同的地方,我不觉得自己是在读书。我尤其喜欢他那些短篇,例如《雨中的猫》,没什么事发生,但是个很美的故事。
南方人物周刊:没什么事发生,但能捕捉人心的微妙变化,你喜欢挪威作家约恩·福瑟的作品吗?
施塔姆:我没读过他的小说,但我读过他三四个剧本,例如《有人将至》等代表作。14、15年前,他那些剧作在德国很受欢迎。我喜欢他的作品,但有时可能没法领会挪威人的那种冷幽默。我觉得福瑟是个非常诚实的人,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读了些关于他的报道。你知道吗?他改信过不同宗教,最后信了天主教,我觉得他是那种敢于面对真实自我的人。
南方人物周刊:你怎么评价奥地利作家彼得·汉德克的作品?他也以德语写作。
施塔姆:我更喜欢汉德克的早期作品,尤其是那本《无欲的悲歌》,讲述他母亲的真实人生经历,她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桎梏,最终选择了自杀。《无欲的悲歌》蕴含着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语调,在德语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南方人物周刊:《在陌生的花园里》中的那篇《看望》,对“空巢”老人的心理刻画细腻而温暖,但也能读出她的孤独和无奈,分享下你当初创作这部短篇的考虑?
施塔姆:我想这源自我对母亲生活的观察。当我在创作中提出些问题时,它可能不是来自我自己的生活,而是我从周边生活中了解到的。因为我母亲就面临着这种生活景况,她有四个孩子,我父亲在我年轻时就去世了,在我母亲生命的最后25年里,她都独自生活。
南方人物周刊:从《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》的结尾和《我们飞》中的短篇《晚年》,都能读到你对独居老人的关怀,现实中瑞士的独居老人过着怎样的生活?
施塔姆:问题在于,他们都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,但正如你所说,这更多是一个情感问题,不像中国,有些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,在瑞士这很少见。瑞士的老人都独自生活,有些独居老人寻求陪伴会养宠物,通常是那种肥壮的大狗,因为老人喂养得很勤,给它们吃得很好。如果这些老人无法自理,通常会被送去养老院。
但有意思的是,我最近因为要写一篇讨论孤独的纪实文本,对此做了些调研。通常就像你说的,我们会想到老年人的孤独境况,但我读到些统计资料,让我感到惊讶:现在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觉得孤独。调研数据显示,在瑞士,18到25岁的年轻人中,有超过60%的人时不时地感到孤独,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,只有30%的人感到孤独。我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能更好地应对独处,现在的我就很享受独处,但二十来岁时我不喜欢独处。
南方人物周刊:这些年轻人备感孤独的原因是?
施塔姆:那篇统计报道中没写,但我认为他们过于害羞、没有社交圈,尤其是新冠疫情那些年,对年轻人而言很难,他们现在整日看着电脑、手机,捆绑在社交媒体上,但基本不出门,我们的两个儿子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,但我发现我们外出活动比他们还多些,他们的学习、工作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,而我们必须出门,家里没什么动静。(笑)
南方人物周刊:我们刚才聊到老年人,与此同时,在《我们飞》等几部短篇中,儿童也是重要角色,说说你对儿童的关注,以及将他们写进作品的考虑。
施塔姆:当我自己为人父母后,我的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孩子这样的角色。需要强调的是,作品中写的孩子并非我自己的孩子,但当我为人父母后,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:为人父母意味着什么?当我成为父亲后,我也开始思考自己与父母的关系,我觉得这改变了我对自己父母的看法。也许,当我养了条狗,我也可能会写更多跟狗有关的故事。
南方人物周刊:我发现,孩子的形象在你的作品中有时也被女主人公视为某种“负担”?
施塔姆:我觉得创作中比较有趣的一件事,是去测试、挑战一些想法。例如,如果你有个自己不喜欢的孩子,会发生什么?你会如何处理和应对?因为要写一个你爱的孩子并不难,人人都知道那是怎样的感觉,但有时在你的生活中,如果那个孩子开始惹恼你,你会如何处理?我觉得去想想这些问题也挺有意思的……